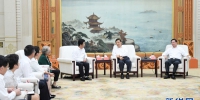塞罕坝的绿色蜕变,始于一批人、一批种子。
因过度开垦和连年战争,新中国成立之初,蒙冀之交的塞罕坝,变成了人迹罕至的茫茫荒原。1962年,为改变“风沙紧逼北京城”的严峻形势,林业部建立了塞罕坝机械林场,希望构建一道护卫京津的绿色长城。127名大中专毕业生与林场原有242名干部职工一起组成了创业队伍。在大中专毕业生中,东北林业大学输送的47名林学系毕业生,包揽了几乎所有本科学历名额,他们用专业知识保障了塞罕坝高海拔地区育种育苗的顺利施行,并见证了塞罕坝的昨天和今天。今年83岁的李桂生,是这47位东林人之一。
骑马也是工作的一部分
1962年,李桂生从东北林业大学本科毕业,被分配至林业部下属的科研单位。他准备好好侍奉年逾七十的父母,让他们度过物质比较优渥的晚年生活。
但当嘹亮的号角吹响,党员李桂生放下个人得失,与其他46名同学一起,踏上了与计划截然相反的人生路,赴一段挥洒热血的青春之约。
同学们搭乘哈尔滨至承德的火车,再坐上“大解放”走土路经过围场县到坝上。仅这段土路,就需要8个小时车程。
47个同学被分成多个小组,分散到各个分场,加入不同的工作岗位。但他们还没开始干活,就已经被难倒了:首先要学会骑马。
人工造林跟骑马有什么关系?这关系还真不是一般的大。
李桂生分担的是总体设计工作,一块空地要种树,种什么树,怎样种,采用人工种植还是机械化种植,都是设计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。一个合格的设计者必须进行实地勘测,掌握空地的土壤、气候、降水等信息,并考察周边地形环境,以进一步确定栽种方式。从驻地到勘测地,动辄单程几十里地,土路难行,也没有小汽车,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就是马。若不会骑马,连最基本的工作要求都无法达到。
“塞罕坝的马,性子特别烈。你这边刚一只脚踩上蹬,马一尥蹶子就跑了,人就被摔下来了。我小时候放过马也骑过马,比别人还稍好些,其他人在这上面可没少摔跟头。”李桂生说,除了马,人们还依赖牛,有时候到比较远的地方勘测,无法在一天内往返,就要架上牛车,拉上锅灶和被褥,做好就地露营的准备。但是黑夜的塞罕坝,是狼群的天下,太阳下山后,狼嚎声此起彼伏,为安全考虑,野外露营次数并不多。
煮鸡蛋是珍馐美味
塞罕坝的冰封期长达7个月,8月份开始下雪。一入冬,本来就难行的土路根本无法通行,过冬的粮食必须在冰封来临前储备好。
当时,塞罕坝人的主食是被当地人叫做“大(音‘代’)王”的发面糕饼,用土法磨出莜麦制成,纯莜麦的叫“大大(音‘代’)王”,二合面的叫“二大(音‘代’)王”。还有一种莜麦面条,制作方法和食用方法类似于东北人熟悉的“酸汤子”,靠工具将面团直接挤进沸水锅里煮成面条。
“现在的莜麦是保健品,身价高着呢。那时候的莜麦吃两口吐一口沙子,杂质多,硌牙。”李桂生说,主食尚且如此,副食更谈不上品种丰富,主要是冻白菜、冻大头菜、冻野菜。有几次馋得狠了,他和同事偷偷到老乡家里买了点鸡蛋煮着吃,竟然觉得是平生第一的美味珍馐。
饮用水问题也是因陋就简,自己动手用锤子砸钻头,什么时候出水就什么时候烧水,有些浅水井可能还不足3米深,新打上来的井水都与茶水一样的颜色,李桂生觉得很知足,有些分场没打出井水,只能喝雪水或是在河沟里取水做饭。
烧炉子睡火炕,这在土生土长的当地人看来没什么,有些南方同学适应起来要困难一些。最让人难受的,是塞罕坝的冬天不但漫长而且特别寒冷。在“白毛风”里外出作业,即使穿上“毡疙瘩”,厚厚的羊皮袄,戴上毛皮帽子,人还是被冻得直打哆嗦。
然而李桂生感叹,吃穿住行的困难都能克服,最怕的是生病,因为能称为医院的地方都远在承德,距离林场有100多公里,遇到发烧急痛的病症,主要靠土方法,根本来不及送医院,能过去就挺过去了。
植一弯翠绿阻挡风沙
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,塞罕坝人仍然完成了两大创举。
“一是在高海拔的坝上成功用种子育苗,二是用机械种植苗木。”李桂生说,用种子育种育苗,是在树苗移栽屡遭失败后的选择,失败再尝试,尝试再遭遇失败,整个科研和实践过程无不浸染了东林人的智慧和汗水。
经过分析比对气候和土壤环境,再经过数次筛选,第一批运抵塞罕坝的树木种子,是来自山西静乐县的2000斤华北落叶松种子。也正是这第一批种子,孕育出塞罕坝的第一片新绿。
“树跟人一样,从暖和的地方到寒冷的地方,它要适应下来才能生存,我们就努力帮助它适应环境。刚开始种下去的树苗成片死亡,活下来的没多少,后来一点点查找原因,一茬茬补种上去,反复这样,后来就是活的多,死的少了。”李桂生轻描淡写的一段话,却让人不由捏着一把汗,看着拼命守护的树苗成片枯萎死去,是多么绝望的心情?
官方数据显示,1964年后,林场种植的516亩落叶松的成活率达到90%以上,李桂生等人终于将提着的心放回肚子里。
让李桂生没想到的是,因为工作需要,他被调到伊春带岭林业局,多年后辗转回到母校东北林业大学直到退休。他与塞罕坝的缘分,竟然只有那最为艰辛困苦的三年。他离开的时候,特意去看了看最早下种的那一批落叶松,最高的已经将近一米,新萌的枝丫在风中轻轻摇摆。
岁月消磨,同学们逐渐被调往各地林业部门,然而有几位同学,就像落叶松一样在塞罕坝落地生根,把青春和生命奉献给中国版图上那一弯阻挡风沙的翠绿。
从一棵树到一片海
李桂生再次踏上那片让他魂牵梦绕的土地是在2002年,参加塞罕坝机械林场建场40年的庆祝活动。此时,他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,而塞罕坝却是愈发青春翘楚,当年种下的那批落叶松已经长成参天大树。
2016年,耄耋之年的他再次来到塞罕坝,过去要坐着“大解放”颠簸8个小时的蜿蜒土路,已经变成平坦开阔的柏油路,仅需一小时车程就能到目的地。当年牛马嘶鸣满地粪便的总场驻地,现在的规模已经如同一座城市,人们住进了楼房,用上了集中供热,餐饮、文娱设施齐全,在夏季,随处可见惬意享受“洗肺之旅”的游客。
塞罕坝每年为京津地区输送净水1.37亿立方米、释放氧气55万吨,是守卫京津的重要生态屏障。它的林木总蓄积量已经达到1012万立方米,所释放的氧气可供199.2万人呼吸一年。同时,它所创造的森林资源总价值约202亿元,成为京津地区重要的防沙屏障和生态旅游之地。
16位曾经共同战斗在塞罕坝的东林人踏上亮兵台,将百万亩松涛尽收眼底。当年那片莽莽荒原风沙草场,已然恣意成112万亩的绿海汪洋。(郭楠枫)